|
|
|
|
 |
| |
 据考古资料,大约在一百万年以前的黄河流域中。下游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着中国远古人类。在陕西的蓝田。北京的周口店、山西的芮城等地,都发现了古人类的遗址和遗骸。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一地区经过十几万年的进化和发展,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即到达原始社会的晚期,在黄河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洛河、渭河。汾河以及黄河下游北部,均是中华文明荟萃的区域。 据考古资料,大约在一百万年以前的黄河流域中。下游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着中国远古人类。在陕西的蓝田。北京的周口店、山西的芮城等地,都发现了古人类的遗址和遗骸。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在这一地区经过十几万年的进化和发展,到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之间,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即到达原始社会的晚期,在黄河中游及其主要支流洛河、渭河。汾河以及黄河下游北部,均是中华文明荟萃的区域。
 (一)人参随人类采集业兴起而被发现和利用 (一)人参随人类采集业兴起而被发现和利用
仰韶文化以其分布之广大,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我国新石器文化中的骨干,它展现了我国母系氏族制繁荣阶段的完整历史。
除以考古成果全面论证仰韶文化之外,在历史典籍中记载着远古时代的传说,更为具体地说明我国原始农业和医药形成的过程。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这个时期。在古籍怕虎通.号》中记载;“古之人皆食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由于禽兽资源不足,猎获困难,难于满足原始人类基本生活的需要,则必须采集天然植物充饥。在此过程中,因食用某种植物而愈疾,或因食用某种植物而中毒,便积累了经验,或吸取了教训,形成了原始的药物知识。因为没有文字,只能口传身授,世袭相沿。关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记述在《淮南子.脩务》之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这些见于史籍的传说,与仰韶文化母系氏族制的各项事业发展情况相印证。伴随着中华民族文明史,人参在仰韶文化中后期作为药物加以应用,是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人类认识自然得益于自然的规律的。
 (二)甲骨文、金文早已记载人参 (二)甲骨文、金文早已记载人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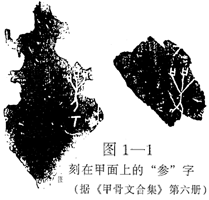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人参,并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应用人参,并最早用文字记载人参的国家。
在我国文字史上,可以辨识的文字以甲骨文为最古老,在商、周时代,把文字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特称之为甲骨文。又称契文。卜辞、殷墟文字。从《甲骨文合集》中查到刻在甲面的“参”字,如图1一1所示。
图1—1中编号为17600、17601两枚甲片的拓片,载于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的《甲骨文合集》第六册2391页(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被收于“卜法”之中。
甲骨文始于商殷时代,据今有3500百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文字记载的内容,多为占卜时候刻下的卜辞,偶有记事的文字。上述甲片上的“参”字是象形字,具有人参植株地上、地下部位的典型特征,且字形粗大古朴,是甲骨文的早期之作。据此可知,我国在3500年之前已经创造出生动形象的“参”字,并有准确可靠的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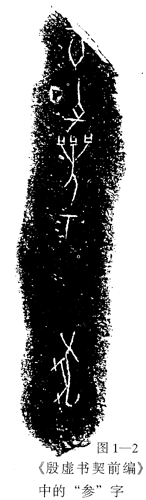 在近代问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虚书契前编》七卷二十五页第四片(简称前七.二五.四)上刻有“参”字(图1—2)。此字在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两书中均有收载。现代大型汉字工具书记载的甲骨文上的“参”字,如图l—3所示。 在近代问世的甲骨文代表作《殷虚书契前编》七卷二十五页第四片(简称前七.二五.四)上刻有“参”字(图1—2)。此字在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两书中均有收载。现代大型汉字工具书记载的甲骨文上的“参”字,如图l—3所示。
我国古老文字中还有“金文”,它是铸造或雕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又有“钟鼎文”之称。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西周的金文字体整齐,辞字渐多,内容多属祀典、锡命、征伐、契约等;战国末年,金文字体渐与小篆接近,一般记载督造者、铸工和器名等。金文中的“参”字在《人参研究》上有专门报道(孙文采,1992),对周早、中、晚金文“参”字有深入的辨析。
在周早的参父乙盉上的“参”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象形字,该字为上下结构,中间一横为地平面,其上为人参地上部分的集中表现,茎上着生多个(古以“三”为多数)核果状浆果,这是人参最主要的植物学特征。地平面以下部分是人参的根茎、主根、侧根,即入药部位。自古以来,对人参均认为“如人形者有神”(《名医别录》),“人参状类人形功魁群草”(《医宗必读》)。该“参”字下部,如同四肢具备的“人”跪在那里。这是人参最形象、最有科学意义的真实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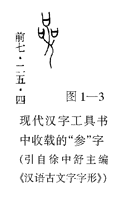
周中舀鼎上的“参”字,其形体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母型”相似。该字省去一横,但地上部分的人参茎和果犹存,特殊之处,是人参之前方多了“三撇”,它代表人参主根上生长有多数侧根和须根,即古人以“三”为多数,在此又有体现。
周晚盠方彝上的“参”字,与周早父乙盉上的“参”字相似,而周晚克鼎上的“参”字与周中舀鼎上的“参”字相似,都是在保留人参地上部分最大特征的基础上,在字形上发生若干变化。及至战国时代,参字的字形与现代繁体字的“参”相当接近,通用简化的“参”字,也保留着象形字的特征。
象形字不是文字图画,不可能把事物十分逼真地描绘下来。象形文字只能抓住物体正面、侧面或局部,使最主要的特征变为线条勾勒成文字。它只像自然物典型之形,经过反复传习,反复使用,逐渐定型、表达语意,在金文中“参”这一专用词有了十分准确的记录。
至于西汉元帝时代黄门令交游著《急就篇》中载有“参”字,决不是“参”字之始。因为该篇问世是甲骨文中有“参”字记载的千余年之后的事情。日本人今村鈵在《人参史》中和日本多种版本的字典、辞典中记载“参”字始载于《急就篇》的观点是不足取的。尤其《急就篇》是本最为初级的认字读物,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具等分类,编成韵语,便于习诵,首句有“急就”(速成之意)二字,故以之命为篇名。就其内容、读者对象、编写目的和文体特征而言,《急就篇》是一本学童用书,在探索字源上没有权威性。但是,用以证明在西汉时代,对于人参已人人皆知,即使在启蒙教育中都在传播“参”的知识,此在人参史上具有更高层次的学术价值。
 (三)人参药用精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三)人参药用精髓始载于《神农本草经》
以仰韶文化中刻在陶器上的符号作为中国文字雏形来计算,中国文字有六干年以上的历史,然而以文字记事、叙事、立论、著述,当由商代(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和周代(公元前8世纪至前256年)的甲骨文为先导。到秦始皇时代统一文字,直至汉代有各类著作间世。其间,有些流传至今。《汉书.郊记志》中记载,在公元前31年已有“本草待诏”的称谓。“本草”泛指中药,因诸药中以草为本之意。在《汉书.楼护传》中叙述,“护少年时候诵读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可知,当时已有本草专著可供学习之用。由于本草知识日渐丰富,经专门人员整理提高,便产生了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不是某一位古代本草学专家所著,其内容之丰富,涉及范围之广泛,决非一人一时所能完成。之所以加用“神农”之名,正如《淮南子.脩务》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于神农、黄帝而后入说。”此与前述“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的古代历史传说相呼应,可以认为,由原始社会到《神农本草经》成书,全部本草学成就,均由该书所统辖,于其中全面反映出史前时代的药物学水平,就有关历史渊源而论,这符合学术上的积累、发展过程,是顺理成章的结果。
在《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着历史上形成的人参药用的精髓,谓“人参,味甘微寒。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一名人衔,一名鬼盖。生山谷”。对此药效精论,现代学者已经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进行了考察验证,确认《神农本草经》中有关人参医疗作用之记载是完全正确的。
《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其中将药物分为三类:上品120种,中品120种,下品125种。就其包罗的药物学知识而言,该书是秦汉以前本草学成就第一次大总结,全面反映了这个时期的药物学成果。后世称《神农本草经》是中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根据其囊括的本草学内容推断,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药物专著,成书年代是在秦汉时期(《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即在这个时代,中国对人参的药用价值已经有了全面总结,形成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达到古代人参史之最高学术水平。
《神农本草经》原书已佚,有关内容在梁代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宋代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都有选载。到达明、清时代,有许多本草学者辑佚,形成了多个版本的《神农本草经》,现有明代卢复辑本,清代黄爽辑本;孙星衍、孙冯翼辑本,顾观光辑本以及日本人森立之辑本。各种辑本对人参的记载甚为一致,且均列为上品。
现代出版的有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点》,王筠默、王恒芬《神农本草经校正》等。关于人参方面的知识,后者较为丰富。
 (四)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四)汉代是我国重用人参的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医药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其间使古代零散的医药经验上升为系统理论,为后世的医药学发展奠定了基础。汉代,涉及人参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以考古资料为根据编著的《武威汉代医简》;在《伤寒杂病论》基础上,由后人辑成的医学名著《伤寒论》等。
1972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县旱滩坡汉墓中,发掘出一批汉代医学简牍,共92枚。其中简78枚,牍14枚,如图1一4所示。考古学者对墓室、棺木结构特点,对殉葬品鸠杖、五铢钱及陶制壶、仓、灶、井、盘等随葬品,与武威县磨嘴子大批汉墓出土文物进行比较分析,判定旱滩坡墓的年代为东汉早期所葬。出土的珍贵文物简牍经过技术处理,除残破者外,所书文字均可辨认。令人欣喜的是,在1枚简、2枚牍上,书写着有人参组成的临床应用复方。
第77号简为断简残文,其内容是:
/梵四两消石二两人参方风细辛各一两肥枣五
这枚断简的全部内容已无法判定,但从其组方特点可知,这是把人参用于解表、祛风、止痛方面的处方,临床上用于外感风寒,表证所致诸多疼痛等病症。可以认为人参与辛温解表药配伍应用,在汉代已是常用的方法。
第82号犊,为正、背两面书写,正面(82甲):
治久泄肠辟□□□□裹□□□□医不能治皆射去方黄连四分黄芩石脂龙骨人参姜桂各一分凡七物皆并冶合丸以蜜大如弹丸先铺
背面(82乙):
食以食大饮一丸不知□□□□肠中□二加甘草二分多血加桂二分多农加石脂二分□一□□□□□多□加黄芩一分禁鲜鱼猪肉方禁良
上列82乙在图1一2中省略。
这枚牍记载着治疗肠辟(即肠澼)下血、辨证用药的处方。肠澼的含义有二:(1)痢疾的古称,(2)便血。本方以清热燥湿药为君,收敛止血药石脂、龙骨为臣,人参、姜桂为佐使,是治疗湿热、痢疾、便血的专方,在强调辨证用药的同时,随证加大原方中石脂、桂、黄芩的用药剂量。
第86号续,为正、背面书写,正面(86甲):
□□大风方雄黄丹沙□石/兹石玄,石消石/长/一两人参/之各异/□三重盛药□□三石□□□三日
背面(86乙):
/热/上□□十□/饭药以/猪肉鱼辛卅日知六十日愈/皆随皆复生/虽折能复起不仁皆仁
这是治疗大风病的处方。大风又称疠风、大风恶疾、癫病、大麻风,即现代所称之麻风病。本方以矿物药为主,是以祛风攻毒立意而需要疗程很长才可收效的方剂。人参在方中协调诸药,以更好地发挥攻毒作用,并可缓和矿物药的毒性,以取得更好的疗效。
《武威汉代医简》中记载的各简牍,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医药著作和珍贵文物,是我国、也是世界上人类记载人参临床应用情况的最早文献,在人参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组方中反映出复方用药、人参有多方面的应用价值,其历史意义更应倍加重视。综合简牍中对人参应用的情况,可概括出有以下突出特点。
(1)人参被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用药规律。
(2)人参的用量相差幅度很大,在剂型和用法上显示着多样化。
(3)普遍使用复方,人参在方中的地位因临床需要而确定。
(4)在人参应用上较《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更加具体而准确,应用范围已经明显扩大。东汉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张机〕对东汉及其以前的中医中药著作去粗取精,结合严格的临床实践经验,于东汉末年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该书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论杂病,提出了包括理、法、方、药在内的辨证论治原则,总结了东汉以前丰富的医疗经验,奠定了中国医药学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对中医药学术思想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东汉时代没有出版书籍的条件,《伤寒杂病论》在辗转传抄中失真分散,至晋代,经王叔和收集整理、编次,形成《伤寒论》一书,这是《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部分。到宋代,孙奇、林亿等进一步发掘古文献,校订了《伤寒论》,又把“杂病”部分整理成《金匮要略》一书。直至现代,《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均为中医界经典著作,且传至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等地。
《伤寒论》中载方113首(实为112首,其中禹余粮丸有方无药),含有人参者,有21首,占总方数的18.58%。《伤寒论》被誉为“方书之祖”,所收载的方剂,具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其中,对含有人参的方剂按现代分类方法加以整理(宋承吉,1984),
可以归纳为以下六类。
1.清热剂 用于清气分实热者有二方:白虎加人参汤方、竹叶石膏汤方。
2.和解剂 属和解少阳者有五方:小柴胡汤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桂枝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方、柴胡加芒硝汤方、柴胡桂枝汤方。属调和肠胃者有三方:半夏泻心汤方、黄连汤方、生姜泻心汤方。
3.理气剂 共二方:旋覆代赭汤方、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方。
4.温里剂 用于温中祛寒者有四方:桂枝人参汤方、吴茱萸场方、理中丸方、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方。属于回阳救逆者有三方:四逆加人参汤方、附子汤方、茯苓四逆汤方。
5.补益剂 仅有一方:炙甘草场方(又名复脉汤方)。
6.驱虫剂 亦为一方:乌梅丸。
通过以上分类整理,可以了解《伤寒论》中含有人参的21个方剂中,其应用范围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作为清热剂、温里剂、和解剂应用人参者,共有17方,占含有人参方剂的80%以上。可知,张仲景运用人参,不是现在人们所认为的多做补益药加以应用,而是以其确切的疗效,广泛用于多种病症。
其次,人参用于“伤寒”、多种热病,在清气分实热、温中散寒、回阳救逆等多种寒、热、逆之急症上均用。即发挥人参大补元气、调营养卫、强心口脱诸项功效,在临床“应急”上占有重要地位。
再次,在和解剂中,无论是和解少阳,还是调和胃肠,均属扶正祛邪、调整机体,发挥多方面药性温和的作用。
张仲景大范围应用人参,扩大其医疗作用,对后世乃至现代,都具有重大影响。《伤寒论》中应用人参的各个方剂,是广泛应用人参的“医方先祖”,直至现代,在临床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以东汉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中业已形成的应用人参的规律和体系为根据,应当认定,我国汉代是应用人参的重要时期。
 (五)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五)唐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高峰期
唐代人参的主产区,在“历史上中国人参资源分布”中已详细述及。唐代的人参应用情况,除《新修本草》中有关人参的论述之外,在大量医学著作中记载得更为全面而具体。而且通过学者和学术上的交流,把中国应用人参的巨大成果传到了日本。其间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孙思邈及鉴真大师。
孙思邈(581~682)是唐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一生拒绝为官,专攻医事。他学识渊博,精通历史、医学和佛学,植根于民众之中,淡于功名利禄,尽心尽力救危扶困,对唐代医药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为历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高尚的医德和光辉的成就,受到后人无限敬仰,尊称他为“药王”,在其故里陕西省耀县立碑建庙。祭祀拜谒,永久纪念。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成书于唐永徽三年(652),其后,孙氏晚年总结近三十年之经验,补充《备急千金要方》之不足,又撰写了《千金翼方》一书。两书除收集唐及唐以前的医药论述及方药之外,尚有大量孙氏本人的临床经验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体会。此外还采录了一些印度、高丽的医学资料。
孙氏在组方遣药中,非常注重人参的地位与作用。在《备急千金要方》中,没有本草学的内容,对人参无专论;《千金翼方》中虽对人参有专条记载,但其内容基本上是《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二者之融合。令人惊奇的是,孙氏在运用人参组方方面,创造了历史上的新纪录,经统计,《备急千金要方》中有445个方含有人参;在《千金翼方》中,有310个方含有人参。
唐王朝全盛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版图扩大,北界包括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西北达里海,东为日本海,历史上特称为“大唐”。其经济和文化交流,遍及欧亚各地。随着唐代文化的传播,中国医药科学也逐渐走向世界。日本以派遣学问增和聘请学者前去讲学的方式,全面学习和接受中国唐代文化。“唐风”在现代的日本仍有相当多的留存。直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医学一直以汉方医学即中医学为主流。中医中药在日本得以存在和发展,其主要根源植于日本医药学始祖——鉴真大师的伟大业绩之中。
鉴真大师师徒们应日本大使和学问僧邀请,先后六次东渡,舍生忘死,战胜重重磨难和险阻,于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大师把佛学、医药学。语言学、哲学、史学、数学.、建筑学以及书法知识带到日本,设佛坛传布戒律,与其弟子一道,广泛传授各个方面的学问,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特别是鉴真大师把中药辨认鉴定、加工炮制、配伍应用、贮藏保管等知识,亲自传授给日本弟子,使日本有了本草学,因而日本医学史记载,鉴真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是日本之“神农”。鉴真当年在日本弘扬佛法。传授戒律的东大寺,至今还保存和修葺得十分完好,其中有一座日本奈良时代的宝物库;称为“正仓院”,该院收藏的宝贵文物中,有大批中药材。以日本药学界近代著名学者朝比奈泰彦为首,于20世纪50年代组织全日本学术水平较高的药学界人士,对每一种中药材都进行了详细研究,将研究成果辑成专著,于1955年以《正仓院药物》为书名正式出版。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该书系统记载了“正仓院北编号为第122号”的中药。
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生药学研究手段,经过精心研究;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第122号中药;大多数是人参根茎(芦头〕,少数是人参根部(主根)。在《正仓院药物》中记载:根茎呈扭曲状,长10~15cm,直径1~Zcm,外表为黄褐色,有多数地上茎凹痕(芦碗)连续、密集、交替地分布在根茎的周围。在根茎的一凹陷处有麻绳贯穿,这是以绳穿人参进行干燥时留下的痕迹。地上茎残痕(芦碗)有10~12个,其分布有不明显的节段性,有人曾以此为根据,将122号中药定为“竹节人参”,即把地下茎(人参芦头)与竹节人参的根茎混为一谈,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令人遗憾的失误。《正仓院药物》的作者们,彻底纠正了这一错误,将第122号中药特征共列出五项,与竹节人参相比较,证明这味中药是真正的人参,而决不是竹节人参。对人参根,在〈正仓院药物》中是这样记载的:根,呈顺体,长约5cm,直径约1.5~25cm,外表为黄褐色。因遭虫蛀,显海绵状。若是栽培品,可能是生长十五年以上的人参;如是野生者,其生长年限则更久。据此,在《正仓院药物》中,日本学者们明确肯定:第122号中药,是产于唐代的人参,如果把它复原,以现代眼光看,它也是最优秀的人参标本(见图1—5)。这是世界上仅存的历史最为久远的人参实物。
我国第一部药典《新修本草》关于人参主产区的记载,《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两部巨著中收载大量应用人参的处方,都令人十分信服,唐代在应用人参方面超过了既往的历史水平。此外,还通过鉴真大师,把我国应用人参的成果传播到日本。因而,唐代应用人参处于历史的高峰期。
 (六)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六)宋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持续期
五代十国的战乱,对经济破坏十分严重。宋朝统治者取得政权后即施行改良政策,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农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商业、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国内外贸易日趋发达。尤其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官办校正书局的成立,为出版包括医药书籍在内的各种书籍创造了条件。在此期间,一方面,国家系统校订、刊行了大量医药著作,另一方面,医药学家个人进行了许多研究和著述,宋代是历史上整理出版医药著作最多。最重要的时期。
宋太宗赵光义(939~997)在即位之前曾留心医术,搜集效验名方千余首,及至登基后,乃诏翰林、医官王怀隐、王佑、陈昭遇等人,广罗单、验、秘方,吸收了宋以前各种方书的有关内容,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于淳化三年(992)刊行。该书共为100卷,1670门,载方16834首,对方剂、药物、病症、病理都有论述,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巨著,对后世有深远影响,被称为集方药之大成的医籍。由于收方浩繁,对其中有人参的方剂尚未统计,但据推断其数量不会低于已问世的其他医药专著。
宋代个人独立编著本草书籍很多,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唐慎微编著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在医疗活动中,“医不重酬,但重得方”,收集到民间和历代本草学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又把北宋政府编修的《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融合起来,在元丰五年门(1082)前后编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32卷,载药1748种,附图933幅,已编写体例严谨,对于药物的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收、炮制、辨析、附方等,皆有详细记载。此书规模巨大,内容详博,药物众多,方药并举,保存了《神农本草经》以下各主要本草著作的内容,是宋代药物学的最高成就。在《本草纲目》问世前的五百余年中,该书一直被视为本草学的范本。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以它为蓝本编著而成的。李时珍对其保存了大量古代药学文献倍加称颂,认为“使诸家本草及各药单方,垂之千古,不致沦没者,皆其功也”。
《证类本草》在人参项下,除对《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收载的内容条理分明地加以叙述外,对陶弘景的注释和《新修本草》的内容也有收录。唐慎微以“今注”的方式说明:“人参见多用高丽、百济者。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亦用焉。”唐氏收录的关于人参的知识还有掌禹锡等谨案药性论的内容:“人参恶卤咸。生上党郡。人形者上。次出海东新罗国,又出渤海。主五脏气不足,五劳七伤,虚损痰弱,吐逆不下食。上霍乱烦闷呕吵,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又云马兰为之使,消胸中痰,主肺萎吐脓及痫痰,冷气L逆,伤寒不下食,患人虚而多梦纷坛,加而用之。”据此论述,人参补虚和对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神经系统门市。脾、胃、心经)疾病的治疗作用,被突出出来,在人参的应用上又向前跨了一大步。《日华于诸家本草》云人参“杀金石药毒,调中治气,消食开胃,食之无忌”。这种见解在说明人参具有解毒作用,可以普及应用,与近世观点十分相似。
《本草图经》成书于嘉祐六年(1061),是《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的蓝本之一,收载人参的内容可谓十分详尽。
在距今九百余年前,对人参原植物的描述及所记载的各个特征,均真实地说明,该书所收载的上党人参就是当代的五加科植物真人参(Panax ginseng C A Meyer)。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证类本草》中所绘的潞州人参(即上党人参)图谱,更无可辩驳地证明,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人参即为五加科人参的见解是极为正确的(见图1—6)。在《证类本草》中,还系统而完好地保留了大量本草学文献,对本草学的考证与研究,对散佚本草书籍的校订、复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见图1—7)。
潞州人参图,以现代植物分类学观点来看,它也是一幅非常典型的人参图谱。根,主根、侧根、须根、根茎(芦)和不定根(艼)都有较为恰当的描绘,即主根呈圆柱形,有明显的横纹;侧根从主根分出,渐细,长度长于主根,这是“顺体”的特征之一;须根与侧根相连,有的自主根伸出,较为稀疏。茎直立,圆柱形。叶轮生于茎顶端,数目依生长年限而不同,叶有长柄,小叶卵形或倒卵形;复叶基部的叶较小,先端渐尖,基部楔形,叶脉显著。总花便由茎端叶柄中央抽出;顶生伞形花序,有十余朵或数十朵小花,浆果状核果隐隐可见。图谱显示,我国古代本草学家对人参全株的植物学特点了解得一十分深刻。由《本草图经晰入《证类本草》的这幅人参图,是世界上最早见于文献的人参图谱,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宋代是我国医药著述繁荣的时代,也是应用人参重要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宋代的人参主产区明显向东扩展,增加了人参资源,而且在边境贸易中通过互市交易,可以获得相当多的进口人参,保证药用之需。根据本草著作记载,这个时期应用人参的情况,基本上与唐代相当,口而宋代是继唐代应用人参达到高峰期之后的持续发展时期。
元朝征服者虽然可使疆域空前扩大,但对经济和医药文化却只能使之处于停顿状态。以元朝较有影响的《世医得效方》为例,其中只有306个方剂应用人参,较历史水平为低。
 (七)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七)明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困难时期
明代自嘉靖到万历年间,由于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扩大,陆路和海上贸易发达,有大批药物涌入我国市场。这一时期医药事业兴旺,有关论著大批问世。在这些著作中,与人参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人参传》,该书是《本草纲目》的编著者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所著。原书已佚,部分内容被收录在《本草纲目》中。
《人参传》在应用人参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反映出明代对人参从理论到应用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人参传》记载:“人参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发之气,天之阳也,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也,其性沉。人参气味具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上,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祛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也。东垣以相火乘脾,身热而烦,气高而喘,头痛而渴,脉洪而大者,用黄礕佐人参。孙真人治夏月热伤元气,人汗大泄,欲成屡厥,用生脉散,以泻热火而救金水。君以人参之甘寒,泻火而补元气;臣以麦门冬之苦甘寒,清金而滋水源,佐以五味子之酸温,生肾精而收耗气,此皆补天元之真气,非补热火也。白飞霞云:人参炼育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之。”
李言闻以中医药基础理论为根据,对人参的应用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论述;进而用于指导临床用药,这在人参史上是仅见的。对以人参为君的生脉散所做方解,以现代医药科学水平来衡量,应当认为是权威性的阐述。在《人参传》中还特别引用孙真人(孙思邈)对生脉散的特殊应用:“夏月服生脉散、肾沥汤三剂,则百病不生。”即生脉散配肾沥汤各三服,夏季服用,预防范围广泛,治疗效果极佳。在现代方剂专著中所载肾沥汤方有两个,一个来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个来于宋徽宗时由朝廷组织人员编写的《圣济总录》。根据李言闻在《人参传》中多次引用孙真人的论述,所言肾沥汤方当来自孙氏名著《备急千金要方》。该书第十九卷载肾沥汤方的组成。制法和适应症是:
肾沥汤羊肾一具,桂心一两,人参、泽泻、甘草、五味子、防风、川芍、黄芪。地骨皮、当归各二两,茯苓、玄参、芍药、生姜各四两,磁石五两。为粗末,先煎羊肾,去肾入诸药,再煎,分三次服。治劳损,咳逆短气,四肢烦痛,腰背引痛,耳鸣,面色黑黯,心悸目眩,小便黄赤等症。
本方中人参、五味子与生脉散组成相同,二方合用,实际上是加大了两味药的用量。其立意以补益为主,兼有祛风、活血、止痛之功用。所言“百痛不生”,以现代观点理解,两方合用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抗病能力,有预防夏季多种疾病的作用。这是李言闻十分推崇的孙思邈在应用生脉饮中的一个创造,对扩大和重用人参具有积极意义。
李言闻对历史上名医名家应用人参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整理,颂扬良方,批驳谬误,发表了深邃的见解。谓“李东垣亦言生脉散、清暑益气汤,乃三伏泻火益金之圣药,而雷学反谓发心炫之患。非也,炫乃脐旁积气,非心病也。人参能养正破坚积,岂有发炫之理?观张仲景治腹中寒气上冲,有头足,上下痛不可触近,呕不能食者,用大建中汤,可知矣。又海藏王好古言,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节斋王纶因而和之,谓参。能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二家之说皆偏矣。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东垣李氏之说也明矣。仲景张氏言亡血血虚者,并加人参;又言肺寒者去人参加干姜,无令气壅。丹溪朱氏亦言虚火可补;实火可泻,芩、连之属。二家不察三氏之精微,而谓人参补火,谬哉。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胜则邪火退。人参既补元气而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何以与甘草、芩、术谓之四君子耶?虽然,三家之言不可尽废也。惟其语有滞,故守之者泥而执一,遂视人参如蛇蝎,则不可也。凡人面白、面黄、面青憔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儒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咳勿用者,寒束热邪壅郁在肺之咳也;若自汗恶寒而咳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于内直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如此评审,则人参之可用可不用,思过半矣”。
李言闻引述应用人参各家之说,进行了详细比较、深入分析,阐发了辨证用药的正确观点。对恰当应用人参,不畏名医立论,力求完善,进行了有理有据的论述与评价,这在辨证重用人参的历史上是一次重大发展,李言闻的功绩不可低估。惟李氏在提到医家姓名时,常名、号并称或名、姓互称,给阅读和理解上带来一定难度。为较好地体会李言闻的本意,对有关问题略加说明。首先,李言闻赞成李东垣的观点,批驳了雷敦的错误,强调治“炫’的有效方法是用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大建中汤。王好古是元代名医,号海藏;王纶是明代官吏兼医家,号节斋。一个说人参补阳泄阴,肺寒宜用,肺热不宜用;一个竞荒谬地称人参补肺火,阴虚火动失血诸病,多服必死。此二人对人参应用价值的认识是错误的。接着,李言闻列举李东垣(名李果,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名张机,东汉杰出医学家,后人尊称为“医圣”)、朱丹溪(又名朱震亨,元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三位权威关于应用人参的见解,进一步批驳了王好古、王纶的谬论。强调对李东垣、张仲景、朱丹溪各家应用人参的成就不能否定,“二王”视人参如蛇蝎的见解是错误的。继之,李言闻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关于人参“可用也”、“不可用也”的观点。之后,解释了张洁古(名张元素,金代著名医学家“金元四大家”之一)、张仲景、李东垣、朱丹溪、王纶等人的诸多见解,同时李氏以肯定的笔触,强调了“必用”人参的适应症。李言闻认为,经过周详地审视区分,什么情况下应用人参,什么情况下不用人参,需要通过全面思考、细致辨证后才能确定,不可偏执一说,更不可武断否定。
李言闻综合明代以前各个名家应用人参的多种见解,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做出了定论,这是人参应用史上的一次较全面的总结。而巨,令人真切地体会到李言闻所强调指出的是人参的补益作用及其医疗疾病的重要地位。李氏论及人参在临床上的应用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a.用于面白、面黄、面青憔悴,属脾、肺、肾气不足者。
b.用于脉浮而沉、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弱细、结代无力,皆属虚而不足者。
c.用于肾虚、气短促者。
d.用于自汗、恶寒而咳者。
e.用于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
f.用于里虚、吐痢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
g.用于自汗、气短、肢冷、脉虚者。
此外,李言闻在应用人参之反、畏、恶等用药禁忌上,也具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列举李东垣“理脾胃,泻阴火,交泰丸内用人参、皂荚,是恶而不恶也”,古方中用四物汤治疗妇女闭经症,加用人参、五灵脂,“是畏而不畏也”,还有“疗疾在胸隔,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李氏对这些突破禁忌的临床用药方法,倍加赞赏,谓“此皆精微妙奥,非达权衡者不能知”。李言闻称赞敢于冲破应用人参配伍禁忌的做法,是发挥人参治疗作用的创造性发展。这些距今四百多年前的见解,当代临床医生和中药界人士仍难于接受,对人参的反、畏、恶等用药禁忌视同“雷池”,不敢尝试着逾越一步。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与探讨,有大量工作需要深入进行。
根据李言闻在人参应用方面的全面总结,可知在明代,我国应用人参的理论、临床辨证用药的深广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自然,这个时期对人参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大,使人参在供需之间产生了突出的矛盾。
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我国16世纪以前药物学知识和用药经验的全面总结,是一部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本草学巨著;已有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字译本传布于世界。李时珍继承家传,发扬父愿,在《人参传》的基础上,对各家本草学的人参精华都做了细致收集和整理,在《本草纲目》中对人参叙述得最为详尽,就其内容精深和字数浩繁而言,人参项下所载超出了《本草纲目》中任何一味中药所能达到的水平。
李时珍在其父《人参传》的基础上,总结历代本草学成果,在人参临床应用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附方”项下,李氏整理出67个运用人参的处方,分别应用于15类病症(宋承吉,1989)。
a.用于气虚欲脱,阴亏阳绝之证,用人参膏。
b.用于脾胃二经各症。用四君子汤、理中汤或与多种药物配伍组成处方,发挥开胃化痰的功效,治疗胃寒气满、脾胃虚弱、胃虚恶心、胃寒呕吐。反胃呕吐。霍乱呕恶、霍乱烦闷、霍乱吐泻、妊娠吐水、心下结气。
c.用于心经各症。以人参配伍,发挥开心益智功能,主治闻雷即昏、忽喘闷绝。离魂异疾、怔忡自汗、房后困倦。
d.用于肺经各症:治虚劳发热、肺热声哑、肺虚久咳、止嗽化痰、小儿喘咳、喘咳嗽血、喘嗽吐血、虚劳吐血、吐血下血。
e.用于产前产后:治产后发喘、产后血运、产后不语、产后诸虚、产后秘塞、横生倒产。
f.用于痢疾:治冷痢厥逆、下痢口、老人痢疾。
g.用于伤寒:治伤寒坏证、伤寒厥逆、夹阴伤寒。
h.用于风证:治筋骨风寒、小儿风痫、脾虚慢惊、惊后瞳斜、痘疹险证。小儿脾风。
i.用于出血证:治出血不止、齿缝出血。
j.用于淋证:治阴虚尿血、砂淋、石淋。
k.用于疟疾:治虚疟寒热。
l.用于消渴证:治消渴引饮。
m.用于酒毒;治酒毒目盲、酒毒生疽。
n.用于咬螫伤:治狗咬风伤、蜈蚣咬伤、蜂王蜇伤。
o.其他,用于肋破肠出,气奔怪疾。
明代杨起。著有《经验奇效单方》,他对人参的认识和应用具有代表性,谓“人参功载本草,人所共知。近因病者吝财薄医;医复算本惜费,不肯用参疗病,以至轻者至重,重者至危”。实际上,是因为人参日缺,参价日昂,医者、患者皆难于随心如愿地应用人参的结果。杨氏强调人参的药用地位:“然有肺寒、肺热、中满、血虚四证,只宜散寒、清热、消胀、补营,不用人参,其说近是。殊不知各加人参在内,护持元气,力助群药,其功更捷。若日气无补法,则谬矣。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有人参在焉。所谓邪之所聚,其气必虚。又曰养正邪自除,阳旺则生阴血,贵在配合得宜尔,庸医每谓人参不可轻用,诚哉庸也。好生君子,不可轻命薄医,医亦不可计利不用。”杨氏申明这些观点的真意:“书此奉勉,幸勿曰迂。”
李时珍则总结式强调: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发热自汗,眩晕头痛,反胃吐食,疾疟,滑泻久痢,小便频数淋沥,劳倦内伤,中风中暑,萎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治胎前产后诸病”。其用途可谓十分广泛,显然,明代及其以前,在人参应用方面的认识,与现代相比,有着悬殊差异。以李时珍整理总结为界,历史上一直把人参与多种药物配伍,将其作为具有多种医疗效能的“将士”使用;而今,则多把人参当作仅有滋补作用的“富翁”相待,希冀借助其药效,达到强身健体、青春常驻。延年益寿之目的。
综合前述各代人参药用历史可知,到了明代,我国应用人参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上已达到历史的顶峰。然而,人参资源却受到严重破坏,供应远远不足。因此,我国在明代,人参的供应和使用已经进入困难时期。
 (八)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八)清代是我国应用人参的衰退时期
满族在我国东北兴起,建立了清王朝。清代统治者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文化上采取野蛮残酷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株连灭族,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火化受到空前的摧残。在医药上,由于知识阶层的思想受到禁锢,被迫面向古典医籍的考据。在本草学方面,限于对既往本草著作的注释、补充、删节和改编,兴起了所谓“考据学”。反映当时医药学成就的本草著述极为稀少,对人参的应用、研究。著述等,也多是因循守旧,遵经卫道,缺乏创新与发展。
前已述及,明代我国人参资源已经遭到全面破坏。至清代,只能使用“辽参”;到乾隆末年,人参的生产与供应已经走向衰退。清朝统治者及其官员们极其腐败摧毁人参栽培业,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官办参业已日渐衰落。
高度垄断,不求发展,摧残人参栽培业,在野生资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使人参的生产、供应、应用均步入难于挽回的境地。清代有代表性的本草学著作《本草纲目拾遗》(赵学敏撰,刊于1765)中,关于人参应用进展情况毫无记载,而在“参叶”项下则指出“今因辽参日贵,医辄以之代参,凡症需参而无力用者,辄市叶以代。故今大行为时,苏州参行参叶且价至三五换不等。以色不黄瘁,绿翠如生,手持之有清香气者真”。这期间,人参主要供高层统治者和富豪们享用,黎民百姓失去了运用“百草之王”防病治病的能力,于是“参叶”身价大增;堂而皇之代替人参药用。
在应用人参知识与理论方面,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一书中有较完整的记载。该书对人参的应用价值归纳为:人参甘温微苦,大补肺中元气,泻火,除烦,生津止咳,开心益智,聪耳明目,安精神,定魂魄,上惊悸,通血脉,破坚积,消痰水,治虚劳内伤,虚咳喘促,心腹寒痛,伤寒,呕吵反胃,淋沥,胀满,多梦纷坛,离魂异疾,妊娠吐水,胎产诸虚,小儿慢惊,外科阴毒,因虚失血。气虚甚者,浓煎独参汤进之。挟寒者稍加附于。按人参功能在诸药之上,但气闭,肺有火热,及肺气不利者忌之。表实;表有邪者忌之。凡痘痧斑毒,欲出未出,但闷热而不见点,若误用之,以阻截其路,为祸尤烈。产辽东。宁古台(塔)出者,光红结实;船厂出者,空松铅塞,并有糙有熟,宜隔纸焙用。忌铁。不宜见风日。
在人参应用理论方面,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中有较多的阐述,他认为“人参性禀中和,不寒不燥,形状似人,气冠群草,能回肺中元气于垂绝之乡”。黄氏批驳“第世畏乎其参者,每以参助火助气,凡遇伤寒发热,及劳役内伤发热等症,畏之不啻鸩毒”的极端认识,认为参以补虚,并非填实,主张在元气素虚,邪匿不出,正宜用参相佐,“用人参内入,领邪外出”。非因外感,而是劳役发热,亦当用参,关键在于“参之所以能益人者,以其力能补虚耳”。强调“虚而气短,虚而泄泻,虚而惊恐,虚而倦怠,虚而自汗,虚而眩晕,虚而饱问食滞等,因当用参填补。即使虚而咳血,虚而淋闭,虚而下血失血,与夫虚而喘满烦躁日渴便结等症”,均可重用人参。用参之道“惟在虚实二字,早于平昔分辨明确,则用自不见误耳”。黄宫绣的一系列见解,主要集中在人参补虚方面,与现代应用人参的观点相近。
摘 自:《中国人参》
|
|
 |
|
|
|

